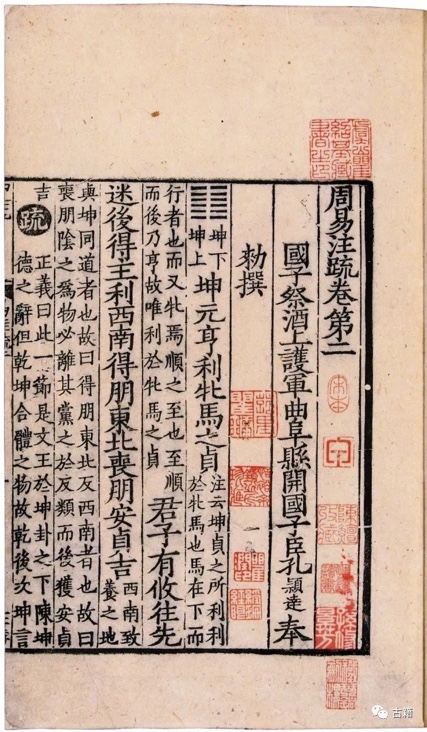
1949年,神州大地翻天覆地,千百年理想的公有制来到眼前,荡涤着旧社会的一切价值观。读书人的神经尤其敏感,以吃公家饭穿干部服为荣,不自觉或自觉地追求进步、自我改造,过去私藏的宝贝顿成烫手山芋,似乎只要赶快扔出去才能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新中国第一拨献宝热潮遂告形成。
开国献宝第一人贺孔才
北平解放不到3个月,194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一则不同寻常的嘉奖令:“北平军管会顷通令嘉奖贺孔才先生捐献图书、文物的义举……本市贺孔才先生于解放后两次捐出其所有图书、文物,献给人民的北平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计图书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册,文物五千三百七十一件。贺先生忠于人民事业,化私藏为公有,首倡义举,足资楷模,本会特予嘉奖。”一下子震动了中国文藏界。
贺孔才出身书香世家,自幼饱读古文国学,是传世古籍和文物的收藏家,青年时跟随齐白石研学治印,屡被齐老夸奖,曾获赞语:“消愁诗酒兴偏赊,浊世风流出旧家,更怪雕镌成绝技,少年名姓动京华。”他曾任过北平市政府秘书、北平市古物评鉴委员会委员、中国大学国学系副教授、河北省通志馆编纂、国史馆编纂。
贺孔才抗战前曾参加过营救同学齐燕铭,解放后倾向进步决心投身革命工作,以献宝国家表示抛下封建包袱告别过去,又改名谢泳穿上军装,47岁成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研究室的研究员,进入武汉参加接管了武汉大学。后来回北京,由齐燕铭介绍到文化部文物局担任了办公室主任。遗憾的是没有等到展示满腹的学问,就在1951年12月不堪冤屈而自溺身亡,40年后才得平反。
周叔弢与霍明治献宝表示进步
1949年8月底,报上又传来了“周叔弢霍明治先生捐献珍藏图书文物,华北人民政府准予表扬”的消息:“继北平贺孔才先生献出图书文物之后,近又有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先生与霍明治先生献出珍藏之图书文物……周叔弢先生将他用二两黄金买来收藏的海内孤本宋版‘经典译文’交由北大唐兰教授转送高教会,与故宫博物院收藏之二十三册合并即成为完整之一部。霍明治老先生将他毕生收藏的图书共一万零七百九十册及珍贵的金石漆器等文物三千九百九十二件捐献给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对两位先生此种化私藏为公有,裨益人民的精神,认为应该表扬,已准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分别发给‘褒奖状’,以资鼓励。”
周叔弢,当时是天津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经理,周氏企业集团的代表者,被称为“北周实业传人”(南为张謇,北为周学熙)。抗战时期,周叔弢虽身在沦陷的天津,但不与敌伪合作,洁身自爱深居简出。抗战胜利后,他复出原想趁国家复兴再展鸿图,没想到才两年又面临了是走还是留的抉择。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已经迫令永利、久大、东亚和启新等大型企业南迁,闹得天津工商界惶惶不可终日,头头脑脑聚在“三五俱乐部”里食不甘味。是跟国民党走,还是留等共产党?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周叔弢与李烛尘率先站出来说话:“叔弢以数十年经营、生活之实践,不能不寄民族复兴国家兴旺的希望于一个新的政权……”他选择了做共产党的朋友。
1949年天津解放后的春天,刘少奇雪夜造访周叔弢,坐在周府书房里品茗交谈,像学生般地讨教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与经济问题。周叔弢也感动地发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就提出的“劳动神圣”、“双手万能”的高见,请共产党一定要记住中国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表示了对中共“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十六字方针的拥护。不光说,还要做,这回献宝,无疑是他重要的实际行动。
新中国开国盛典,周叔弢被选为工商界的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又以花甲之身当上了天津市的党外副市长,直到文革后还以九十高龄担任了天津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1984年2月24日在医院仙逝。周叔弢早在1982年就立下了遗嘱:“……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发讣告,千万不要开追悼会,千万不要留骨灰盒,投之沧海以饱鱼虾,毋为子孙累。存款五年定期壹万元、国库券壹万五千元,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北周传人,身外之钱竟然只剩如此小数,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的产业也早就献给了国家。早在1942年,他就立过遗嘱要把呕心沥血的珍藏“举赠国立图书馆”,解放后分4次向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捐献了全部的珍藏,也把一生献给国家。
丁惠康捐赠清华大学
为了配合开国盛典,北平一解放就启动了文物宣传,从8月起先后举办了“帝后生活史料”、“抗日史料”、“美帝侵华”、“赵城藏”、“人民捐赠文物”等11项文物展览;其中“人民捐赠文物”,是北平解放半年来各界人士捐赠的16962件文玩的一小部分。11月4日,清华大学又举办了“台湾、西藏及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展出的500多件珍贵文物中有200多件台湾高山族文物,包括木、竹、陶、皮革、金属、纺织、贝壳等材料的宗教法器、房屋构件、饮食器皿、武器、衣饰、雕像、模型、玩具和书籍资料等等,都是丁惠康所赠送。
丁惠康,著名国学家、医师丁福保的次子,自幼受家庭熏陶学医从医,抗战前主编过医学杂志,创办过上海肺病疗养院、上海虹桥疗养院,曾任中国保健协会秘书长等职,在日军侵占上海后,收藏保护祖国珍贵文物,据说曾拒汪精卫妻子陈壁君捐赠,有“三拒汪伪”的正义之举。在宝岛光复后,他请专人到台湾采集高山族文物,在沪、杭等地举办展览。
清华大学举办“台湾、西藏及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独缺台湾高山族文物,于是专程找到丁医师,请求借作“庆祝解放展览”。丁惠康到北平参观了清华大学的文物后,慨然捐赠了收藏的全部高山族文物。回上海后,又向国家捐赠了1尊西周青铜大鼎,并解囊帮助国家收购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著名石刻拓本和孤本书籍1100余册,接着又向故宫博物馆捐赠了全部家藏。
到1949年底,又传来了“冯大生等捐献文物,文化部拟颁予褒奖状”的消息:“大兴县冯公度先生的遗族冯大生等,秉承冯先生遗志,将珍藏的古物图书,其中包括有“周召康公”玉赤刀一柄,玉发箍一件,石屏二件,散氏盘毛公鼎铭文刻石二方,暨冯先生生前纂刻金文砚一百四十三方,图书一七六五○册,捐献人民政府……为了表扬冯氏这种化私为公,爱护人民事业的精神,文化部并正拟颁发褒奖状,以资表扬……堪为收藏家效法。”如此的献宝热潮,一直持续到文革前……陈叔通、马叙伦、柳亚子、杭州钱塘“六唐人家”后人、宁波萱荫楼主人李庆城、晋江陈盛明、陈盛智兄弟、陶瓷学专家陈万里、吴蕴初家属、顾丽江夫妇、藏书家陆心源后代、古玩名人钱镜塘、孙煜峰……在那个家藏古玩如怀抱地雷的年代,化“私藏”为“公藏”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附:他们因何而奉献——也谈建国初期的献宝热潮
作者:陈福康
1月14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何季民先生的《开国时的献宝热潮》一文,提供了一些史料,读后有收获。不过,我对文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见。
何文一开头就说:“1949年,神州大地翻天覆地,千百年理想的公有制来到眼前,荡涤着旧社会的一切价值观。读书人的神经尤其敏感,以吃公家饭穿干部服为荣,不自觉或自觉地追求进步、自我改造,过去私藏的宝贝顿成烫手山芋,似乎只要赶快扔出去才能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新中国第一拨献宝热潮遂告形成。”又说:“贺孔才……解放后倾向进步决心投身革命工作,以献宝国家表示抛下封建包袱告别过去……”“如此的献宝热潮,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在那个家藏古玩如怀抱地雷的年代,化‘私藏’为‘公藏’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以上第三句也许是讲“文革”期间,但何文整个谈的则是“开国时的献宝热潮”。何文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献宝热潮遂告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献宝人“神经敏感”,觉得宝贝放在家里“顿成烫手山芋”,甚至就像“怀抱地雷”,因此,只有“赶快扔出去”,就像“抛下封建包袱”一样,才是最好的选择。请注意“扔”和“抛”这样的字眼。如此说来,当时那些献宝的人其实是出于无奈的,甚至是心怀恐惧的,即使有人“自觉地”献宝,也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进步决心”,其实不过是赶紧“扔抛”而已。那么,“开国时的献宝热潮”也就不值得肯定了,那些捐献者也不值得后人尊重了,只是需要同情、可怜而已。
我认为,这是与历史事实不合的。
何文提到的周叔弢、丁惠康两位,我知道他们的捐献大多是通过他们的朋友、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进行的。我看过他们当时的通信,和他们后人的回忆文章,都说明他们捐献文物和古籍完全是自愿的,是心情舒畅的,是为了表示衷心“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
我想举一位当年属于年岁最大的献宝人之一的张元济为例。他是不必“以吃公家饭穿干部服为荣”的吧。张元济当时除了将以前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珍藏的一些善本书通过郑振铎捐献给国家以外,还多次捐献家藏文物。例如,1953年4月6日张元济致郑振铎信中提到:“家藏元儒谢先生应芳手书佛经六种,书法极精,历六百年金纸如新。藏之私邸,决非长策,合亦献归国有。”“先九世祖讳惟赤于清初中试,顺治甲午科顺天乡试举人,当时领有鹿鸣宴银质杯盘各一事,制作甚精。藏之寒家,适满三百年……询之友人,传世科第者亦云从未目睹……此为国家典章数百年之遗物,窃愿归诸国有。”像鹿鸣宴银质杯盘这样的家藏宝贝,如果在极左的年代,是会被看做“封建”的东西的;但张元济当时却绝不是当它为“烫手山芋”,而是作为“国家典章数百年之遗物”而真诚地敬献给国家的。
我还想举戏剧家吴祖光父子为例。2003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他写的《我的冬天太长了》一书。在这本书里,有一篇《241件文物捐献记》,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初,吴祖光从香港回到北京,就与瘫痪在床的父亲吴瀛商量,怎么安置老父亲几十年颠沛流离中保全的一大批珍贵字画文物。“我对父亲说:‘新中国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世代期望终于出现的一个完全可以代表全民意志的廉洁的理想的政府。这批宝物由我们自己保管、照顾都十分困难。我的意思,全部捐献给国家好不好?’父亲完全明白了,他满面笑容,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吴祖光就到文物局向郑振铎报告,请郑到家里来鉴定。第二天,郑振铎就偕同唐兰到了吴家。“郑先生对我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经过兵荒马乱,居然保存至今,实在难得。’他问我是否与父亲商量过,需要国家付出多少代价来收买?我没有和父亲商量过,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国家付出代价的问题。我立即回答说:‘是无偿捐献。不要任何代价。’虽然那时我出于买房子还有一笔几千元的负债有待偿还。但是我认为人民政府是旷古未有过的人民自己的政府,不能向政府要钱。”吴先生当时对父亲、对郑振铎说的话,吴先生现在写的文章,无比雄辩地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献宝热潮”形成的原因。
本来,我还想引用郑振铎本人在建国初向国家捐献一大批自己珍藏的陶俑时,写给周总理的一封信等。但想想,吴祖光先生的话已经足以代表所有的献宝人了,也就不再去查找郑先生的信了。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的“献宝热潮”,主要是出于人民衷心的爱国热情,是完全自愿的。这是美好的佳话,对捐献者的化私为公的崇高精神更是应该充分肯定。(而“爱国”这样一个神圣的话语,在何文中一点也未看到,令人感到奇怪。)另外,“献宝热潮”似乎也不止“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其后也是有的,不过从规模上来说没有建国初那样密集和巨大。例如在现在的上海博物馆展览厅里,就有不少近三十年来的新的捐献。我们对那些捐献者充满崇敬。我们不能亵渎建国初期那些捐献者崇高的真诚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