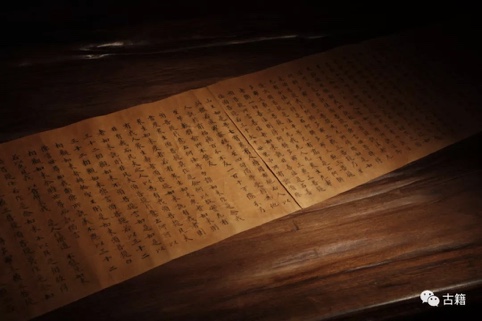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敦煌写本的研究有了重要的进展。1953~1954年,山本达郎教授和榎一雄教授在东洋文库的资助下,将斯坦因收集品全部用缩微胶片进行复制,这标志着敦煌学研究在日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几乎与此同时,东洋文库也获得了北京收集品的部分缩微胶片。近年来,这些收集品的大部分都已陆续编成目录。在1960年第15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列宁格勒收集品首次公之于世,令人瞩目,因为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这些缩微胶片和目录,使我们能够对一个洞窟中掩藏的书室原貌有了大致的了解。目前,在敦煌本地也建立起了一个对这些佛教洞窟进行系统研究的研究所(原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译者),而且被称为“敦煌学”的学科中,已包含了对当地古代文物的调查。敦煌文书也的确应与其出土地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本世纪前半叶,对敦煌写本残卷的传统研究方法是“觅宝”式的。现在,随着遗书的陆续公布,必须让位于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将写本残卷重建为一个整体,并且找出个别写本或写本群在全部遗书中的位置。这种研究途径将对中国目录学做出新的变更(过去常局限于印本书籍),并且将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置于坚实的基础上。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总括地考察石室写本,这是敦煌学迄今一直忽略的一个方面。
我所在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1956年从东洋文库得到斯坦因收集品的放大照片后,组织了一个敦煌写本研究组。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该收集品进行编目,因为当时翟林奈的《目录》尚未问世,而大部分写本均为断片,也没有标题。我们当时对写本作了简要的目录学说明,包括每组写本在形式和文字上的特征。这份说明性目录在校勘和最终付梓前,曾经油印成册,其中一部分已刊载在各种杂志上。另外,在1964年出版的一期《东方学报》“敦煌研究专刊”上,也刊载了几篇文章,就是此项工作的研究成果。我现在所进行的考察研究,有许多内容需归功于这些已经发表或尚未发表的资料,我在下文将还会提到。
另外,在1964年秋,我对欧洲和印度的敦煌藏品进行访问参观,也是促成本文的一个因素。在这里,我想向下列人士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是:列宁格勒的孟列夫教授和丘古耶夫斯基先生,英国博物馆的欧立克·格林斯泰特先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汤普森小姐,巴黎国立图书馆的隋丽玫夫人,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的埃尔丝·格米尔夫人和欧立克·赫尔先生,新德里国家博物馆的班内杰博士和考尔先生,以及上述馆中的摄影服务人员,他们非常辛苦地向我提供了藏品的复制件。
最重要的,我想向剑桥大学的龙彼得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他在京都短暂的逗留期间,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本文的英文稿进行了订正,对文中的某些表达方式和细节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另外,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约翰·布劳夫教授对本文的校对也付出了劳动,对此我也深表谢意。
一、敦煌写本目前的下落
1.斯坦因收集品
敦煌写本的斯坦因收集品,主要来自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1906一1907年进行的第二次探险,这些写本现存于伦敦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现在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译者)中。而斯坦因探险中的考古发掘品的绝大部分,现存于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中亚部中,即原中亚古物博物馆,只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标本存于英国博物馆中。但是,由于这些写本并不是作为考古发掘品被送往伦敦的,所以写本的汉文部分存于英国博物馆,而藏文、梵文、于阗文等则保存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中。
保存在英国博物馆中的汉文写本,已由已故的翟林奈博士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工作编成目录,并在其谢世后出版。在这部目录中,翟林奈抛开了写本上原有的“ch·x·11”式样的编号(斯坦因探险时所做的编号),而按照“S1~6980”的方式顺序编号;此外,又根据他的分类整理,在目录中重新编号。总的来说,这部目录编得很好,分类合理,定名也长短适中,而且对每件写本的年代推断也有其正确性。但是,因为翟林奈对佛教经典不太熟悉,有几百件佛经写本断片未加比定,对一些写本在经文中的章节也无法确定,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老写本在如何分卷上并不一致,而且与现在的版本也有所不同。更为严重的是,他把缮写者丢弃的废纸也都认为是当时的正规写本断片。此外,在非佛经写本的分类编目中,无论官府文书还是寺院文书,都需要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进行重编。
如前所述,写本的原始编号是以“Ch·x·11”的方式编排的。然而,斯坦因在1913年第三次探险期间,从道士王圆篆那儿得到的保存完好的500件写本,却编有不同的探险号码,即“Chien·001”。对此,翟林奈采用博物馆编号的方式,都加上了字首S。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约在1920年前后,他又改变了编号方式。在1913~1916年和1922~1923年期间访问过伦敦的矢吹庆辉,在言及写本时经常采用博物馆的旧编号。翟氏改变编号的目的,大约是想把斯坦因第一次和第三次探险所得写本(各自为S.5862一5872和S.6482一6963)统一并入这个编号系列。其中书籍形式的写本编为S.5431一5480和S.5498一5700号,S.5873一6481和S.6964一6980号则为断片。此外,另有大约3000件碎片根本没有编号,这些碎片正由格林斯泰特先生进行编目。最后,属于印版和八种语言混写的写本,虽然也进行编目,但并未包括在S系列的编号中。
其他种文字的写本,收藏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中斯坦因藏品的单独书库中,其中大部分为藏文,梵文和于阗文的写本则并不很多。属于藏文的写本,按照写本的原始式样订成73卷(数码列到74,但其中有一个号码未使用),有的呈长方形,有的呈方形。这些文书或是印度贝叶形的,或是中国卷轴式的,每件写本上还都保存着原探险时的编号。另外,还有大约1000件左右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本,原来是卷轴式的,现在则已折叠装订成册。
藏文的佛经写本已由已故的路易·瓦雷·普散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居留伦敦期间编目描述,但是他的《目录》直到最近方才出版。这本《目录》属上乘之作,分类合理,且对残片都进行了鉴别,并提供了每件写本首尾行的录文或转写,还提到了这些写本的近代版本和重要的研究参考资料。作为该《目录》的附录,对一些藏文或于阗文写本背面的汉文写本残卷也进行了描述,这136件写本的详细情况是由榎一雄教授提供的。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并未出版非佛经写本的目录,因为这些写本的大多数已由其前任馆长F·W·托玛斯作了汇编,大部分于阗文的写本由H·W·贝利教授刊布,现已出版了6卷。
2.伯希和收集品
在斯坦因离开几个月之后的1907年12月,保罗·伯希和来到了敦煌。在对佛窟进行调查后,于翌年3月,他购买了几千件写本。这些写本现藏于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其汉文写本的编号从P,2001开始,因为编号P,1一2000是为藏文、粟特文等写本保留着的。但是,因为后者的数量远远超过了2000,所以,现各种不同文字的写太都加上了字首,即“伯希和汉文文库”(PelliotChinois)、“伯希和藏文文库”(Pelliottibetain)、“伯希和粟特文文库”(Pelliotsogdien),等等。编号为2001~3511以及4500~4521的汉文写本,是由伯希和自己在探险后不久进行编目的,目录的副本分送给一些中国和日本的学者,他们广泛地使用了这个目录⒁。这些写本的大部分,也采用图版或印刷制版的方式发表,其中一些编号相继由王重民和那波利贞进行了编目。但是,直至伯希和谢世之前,还有几百件卷轴写本由他自己保存着。1962年,王重民最终将其所得的这些写本目录的副本,编入1962年上海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这本目录虽然极为概略并欠完整,却使我们能够对伯希和收集品的全貌有个整体的了解。
现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在两位中国学者的协助下,正在编一份新的目录。1964年我在巴黎参观时,已见到目录的第一部分,即从2001~2249号的校样。这份新目录虽然相当详细,但是没有述及写本的书法和纸质,而这些内容在完整的编目中是不可缺少的。
藏文写本的编目,由拉露小姐汇编成三册出版,包括1~2216号。但是,另有几百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本仍未编目。这份详细的目录,每一册出版的间隔时间大致为10年左右;其每条目录除了对写本的特征描述和比定外,还提供了每件写本的首尾几行的录文。
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等文字的写本并不多,虽然没有进行专门的编目,但其中大部分已在期刊杂志上刊布;有些粟特文写本的图版;已由高狄奥和邦旺尼斯特刊出;于阗文的大部分写本已由H·W·贝利刊布;哈密顿正在着手汇编回鹘文写本,其他文字的写本也准备汇编出版。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双语写本分别有两个系列号,因为这些写本是作为汉文写本编号的,后来又编入其他系列号,例如:P,Chinois2021=P,sogdie10,P,Chinois2046=P,tibetain1257等等。
法国国立图书馆对敦煌遗书的保管工作大概过于彻底了,其中大部分是裱装在中国纸上,正面覆以细绢,同时上浆硬化。所以无法研究原来纸张的质地。该图书馆规定,读者每次只能查阅十件卷轴,这就使得学者不可避免地只能“觅宝”,而不能将全部写本作为整体来进行研究;而另一方面,英国博物馆(该馆对写本并未做如此精致的裱装)的人员却抱怨,有些写本因经常查阅而严重破损。
另一个问题则产生于收集品本身。伯希和在敦煌是从研究汉学的角度来筛选写本的,这样,在巴黎的非佛教文献写本要比其他收集品多得多,这就使得学者们在半个世纪中,都只把敦煌写本作为汉学的一个宝藏,却不能把它看作是目录学和一个知识资源。当然,一些小学生习字的写本是不适合用于对中国古籍进行校勘的!
3.北京收集品
北京的中国当局开始时对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发现并未在意,但是,当后者在1909年将部分写本带往北京进行修补和装裱并展出时,当局大吃一惊。清政府的学部立即通令甘肃藩司,将所有剩下的汉文写本运往首都。这样有近一万件写本入藏北京图书馆(即当时的京师图书馆——译者)。据说,有许多写本在运送途中被窃。大约20年以后,在中央研究院主持下,由当时最有名望的佛学专家、图书馆馆长陈垣进行了编目。这些写本在送往北京前,已由甘肃当局用《千字文》开头的88个字作为字首,进行了编列,每个字首编为l~100号(共8679号)。由于藏品有大量的佛经写本,所以此目是按“佛藏”系统进行分类的。每个条目中,将各种经文的开始两行的两个首字和结尾两行的两个末字录出,有的条目附有简单的描述;对大多数写本残经都进行了比定。
由陈垣比定著录的写本,常被称为“第一组”。几年以后,胡鸣盛开始对较小的残片(1192件)进行编目,这些残片在已出版的目录中被省略了,但他也似乎没有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他的一位同事许国霖,则对佛经写本的题记和其他写不上的文书做了汇编,其中包括“第二组”中的一些写本。北京图书馆最近显然又获得了1000多件写本,这些写本迄今尚无目录发表。
几年前,北图藏卷所谓“第一组”的缩微胶片已复制成,并且分送欧洲和亚洲少数一些地方。因此,在我们进行的写本研究中也可以加以利用。我们已经注意到,这里的藏品与其他处的藏品相比,其中的残片拼接缀合率较高,可以重新合成较大的单元。值得一提的是,佛经写本中带有题记的要比伦敦和巴黎的为少。很显然,藏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也较少。
4.大谷收集品
大谷探险队及其发掘品,有着一段复杂的历史。已故的佛教净土真宗教派的门主大谷光瑞伯爵派出的三次印度和中亚探险队,其目的是搜寻佛教遗迹。1902~1904、1908~1909和1910~1914年的三次探险,并不是以政府或大谷寺院的名义进行的,而是在他自己的倡导下进行的。探险队的成员都是受过他私人教育的男孩子,如第二次和第三次探险的队长橘瑞超,在进行第二次探险时年仅17岁。
在第三次探险过程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橘瑞超音信全无,大家认为他可能在新疆失踪了。因此,大谷又派遣他手下的吉川小一郎去寻找。1911年2月,他们二人在敦煌相遇,得到了包括汉文和藏文的几百件写本。
大谷的收集品,其中包括在吐鲁番发现的写本经及其他一些考古发掘品,开始时保存于大谷在神户郊外的别墅“二乐庄”内,后来其中部分搬运到旅顺港。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避免为这些“古董”付进口税,因为旅顺港是个自由港。有几年时间,探险队成员既在神户又在旅顺港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不久,大谷就出版了一本大图册,其中包括诸多写本的图版;由橘瑞超编的一个佛经丛书也系列出版。同时,橘瑞超编成了一份汉文写经目录,并由罗振玉在1914年出版。但是,有关考古探险队成员的日记和其他文字记录则直到1937年才出版。
后来,大谷失去了研究中亚的兴趣,其收集品也移入旅顺博物馆。现在,这部分藏品已由中国政府接管,目前我们也没有一这些写本最后下落的确切消息。
大约在1921年,为了继续在京都的学习,橘瑞超离开旅顺,同时将他主要是在吐鲁番获得的两箱文书带到京都。然而,他的导师却派他到上海去。这样,这两个箱子似乎被遗忘了,直到1947年大谷逝世后几年,人们才在京都的一个仓库内发现它们。后来将这些文书赠送给净土真宗教派的学院——龙谷大学,以供研究之用。其他一些用汉文、梵文以及藏文等写成的佛经,总数在100件以内,早在1930年以前即作为标本送往同一学院。1950年,在石滨纯太郎主持下,该学院成立了一个研究会,对文书进行研究,并出版了六卷本的研究成果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包括带有对文书进行说明性的文字图版,对敦煌发现品的多方面研究,以及对中亚历史、语文和考古学总体的具有创新的研究论著。这一系列出版物的目的性比较强,其中既有第一流的成果,又有不尽人意的泛泛之作。
5.列宁格勒收集品
俄国收集品的汉文写本来源有三:奥登堡的敦煌探险,科兹洛夫的黑城子探险,以及克罗特科夫和马洛夫对吐鲁番的探险。这些写本入藏于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写本部,并统一编号,其中敦煌写本占藏品的绝大部分,这是奥登堡在1914~1915年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写本。在十月革命后的许多年中,均收藏在列宁格勒科学院的亚洲博物馆内。对这批写本没有进行过一般性报道,只有极少数外国学者曾见到过极少的几件。在为纪念奥登堡诞辰五十周年而出版的纪念文集中,他的学生们在总传其一生的学术贡献时,虽然从多方面描述了他在1909~1910年的第一次探险,但却只字未提及他是如何获得这些写本的。后来,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于1930年改组为东方学研究所,直到最近才用现在的名字。这期间,K·K弗路格对一小部分藏品进行了编目,但这项工作由于他的谢世而中断,因此余下的藏品也不为世人所知。直到1960年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上,才将藏品的主要部分展示于外国学者面前。与此同时,人们才知道,在现代中国文学专家孟列夫先生的主持下,1957年曾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已经开始对这些藏品进行编目。作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孟列夫在196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对两卷写本中的变文和一个赞文集做了研究;也是在同一年,又出版了该收集品的第一本描述性目录。这个目录是据打字本印成的,其中的汉字采用手写体。目录有2000多条,约占藏品的五分之一,其分类系根据写本内容,采取与翟林奈类似的方法,每条目中有相当详细的注记,并附有每件写本首尾一行的录文。1964年,当我在列宁格勒访问时,第二本目录正准备出版,同时,该组研究人员也正准备出版其他文献和官府文书写本。
登堡收集品的大部分很残破,在第一本目录中,三米长的卷轴本不到百分之二十。原因可能是奥登堡访问敦煌是在中国人已经将更为完整的写本送往北京之后,所以他仅搜罗到遗留下来的残卷。
据孟列夫说,奥登堡还得到了几百件藏文写本,其中大部分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这些佛经作为另一系列保存在同一部门。
6.留存敦煌的写本
尽管最早的报告声称,中国当局在1910年已将所有遗留下来的写本运往北京,其实这并不是事实,因为在俄国人探险之后,仍有几千件其他文字——主要是藏文——的写本留存在敦煌。看来,中国当局关心的只是汉文写本。直到上1919年,甘肃地方官府听到有一个游客买走许多写经的消息后,才派手下的督察员考察当地的实际情况。督察员在那座三层建筑的第二层南侧的佛窟中,找到了94捆,重约405斤的藏文卷轴写本,以及重1744斤的11套夹在木板中的纸本。他留下了90捆,并且把3捆卷轴本和10套夹板迁移到敦煌的一所学校,只将1捆和1套佛经带往兰州,保存在省图书馆中。这里再强调指出的一点是,敦煌存留的写本的重量可能要超过一吨,毫无疑问要超过任何其他各处的藏品数量。
7.小收集品
在上述收集品之外,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图书馆内,也保存了来自敦煌的13卷佛经写本,这可能是亚洲以外值得一提的唯一的小藏品。这些写本是由索仁森先生在1914年前后,在中国的内地、藏北、新疆、戈壁和西伯利亚旅行途中经过敦煌时获取的。如同通常情况那样,每件卷轴的前部已残失,其中有3卷还保存着原来的末端的轴芯,2卷还带有9世纪的题记。福克司教授曾为这些写本编成一份目录,但迄今未见出版。
在日本还有数百件到几件的大小不等的收藏品,但就其中我们所能见到的而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是膺品。它们常常盖有敦煌写本极有名的收藏家李盛铎的印鉴,如“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或“木斋审定”。我发现,前面那个印章有诸多不同的形式,其中只有一个是真品。李盛铎是主持将敦煌写本运往北京的学部大臣的岳父,副大臣曾向朝廷控告他有借机行窃写本的罪行。但是,后来由于清政府很快被推翻,李盛铎也逃脱了困境。他的藏品因为有许多精致的卷轴而名噪一时,其中一些是由一个姓陈的人在李家伪造的。1937年他谢世后,其部分藏品据说卖给了日本人,但现在一直下落不明。
8.原始藏室
现在保存在上述各处藏品中的写本数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散佚的约二、三千件,这就构成了原始的敦煌藏经洞。此外,还有大量的画在丝帛或麻布上的绘画、织锦、铜像和石刻拓片等。
这些写本为什么被弃置?藏经洞又为何封闭?伯希和认为,敦煌封藏这些写本,是由于11世纪西夏人的入侵。斯坦因却持不同观点,他把藏经洞描写为“神圣废弃物的存放处”。比较而言,斯氏的观点更合理一些,因为我们找不到理由来解释僧人们要对西夏人隐藏佛典饰物的原因,因为西夏人大概在来到敦煌以前已饭依佛教了。从大部分的卷轴、绘画、织锦的保存状态较差的情况来看,它们一定在洞中堆积了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些写本过于神圣,不能随便抛弃或挪作他用,所以只能这样收藏。11世纪早期,当对这座三层建筑后面的主窟(第16号窟)进行修复时,洞内的这一大堆数量太多的写本无法迁移到他处保藏,便将藏经洞(第17窟)垒墙封住并且在外面建造一条漂亮的通往主室的甬道。另外,必须指出的是,写本中的藏文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那些汉文本,在当时不具有任何实用价值。
来源:公众号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