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御医医术高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陈可冀教授旧文:
御医的医术高明,临床诊治,首重疗效
原标题:太医难当
——从清代皇帝有关医药的硃批(谕)看御医
陈可冀 周文泉 江幼李
御医的医术高明,临床诊治,首重疗效
原标题:太医难当
——从清代皇帝有关医药的硃批(谕)看御医
陈可冀 周文泉 江幼李
御医,又称太医,因主要在宫中为皇家诊治疾病而名。由于接近当朝统治者、宫帏森严以及种种历史原因,人们对御医的了解甚少,从而有许多揣测。尝有“翰林院文章,太医院药方”之传闻,认为御医处方平平,应景而已,人情练达为主,疗效尚在其次;亦有“太医难当”之说,“伴君如伴虎”,以致历代不少名医均因此不应诏而远遁;尚有认为御医侍奉于君王左右,地位至尊至荣者。清代,宫廷内部明争暗斗激烈,政治风云诸多变幻,帝后死因不明者多,因之御医与政治的关联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凡此种种,均表明人们对于御医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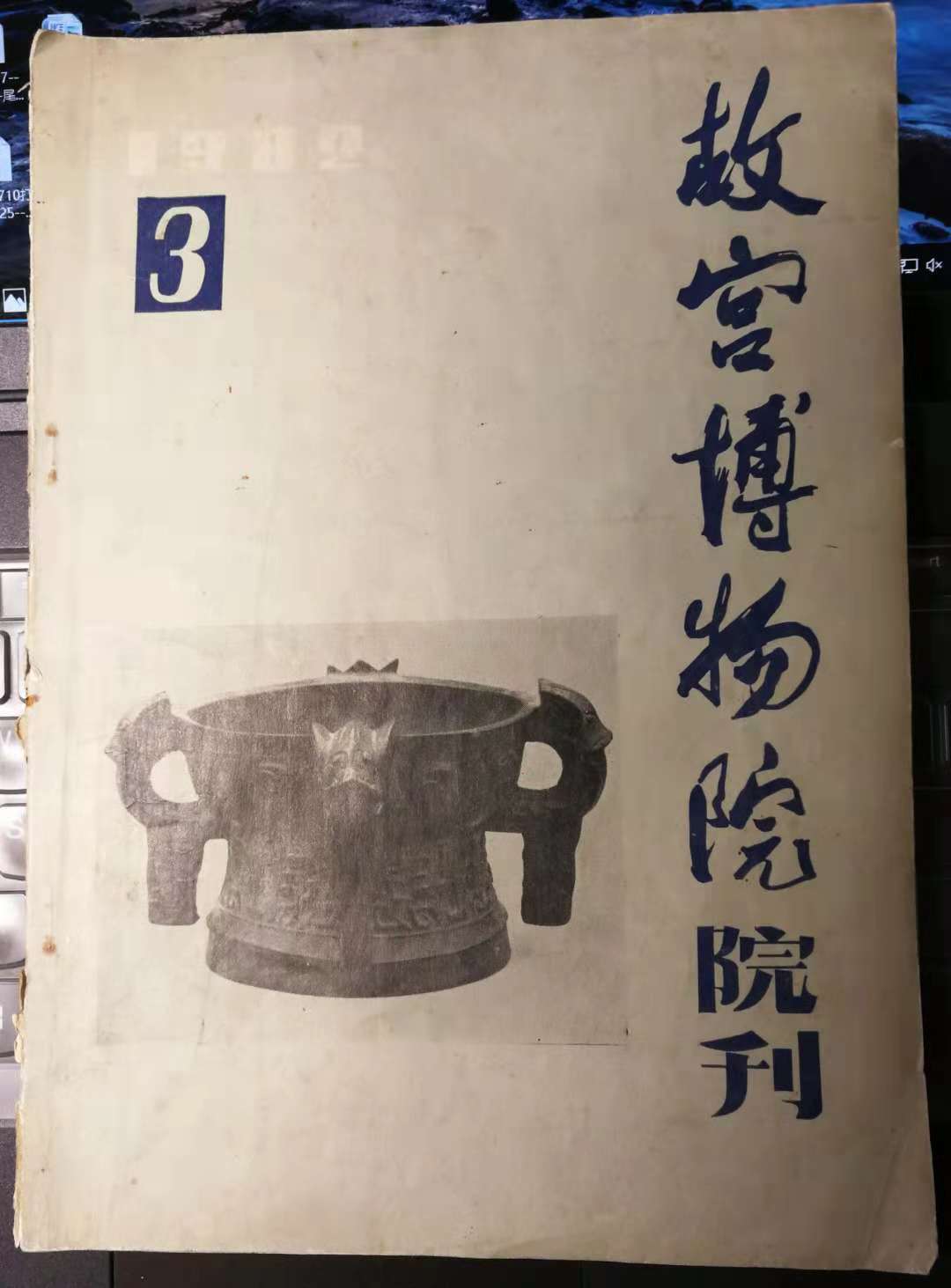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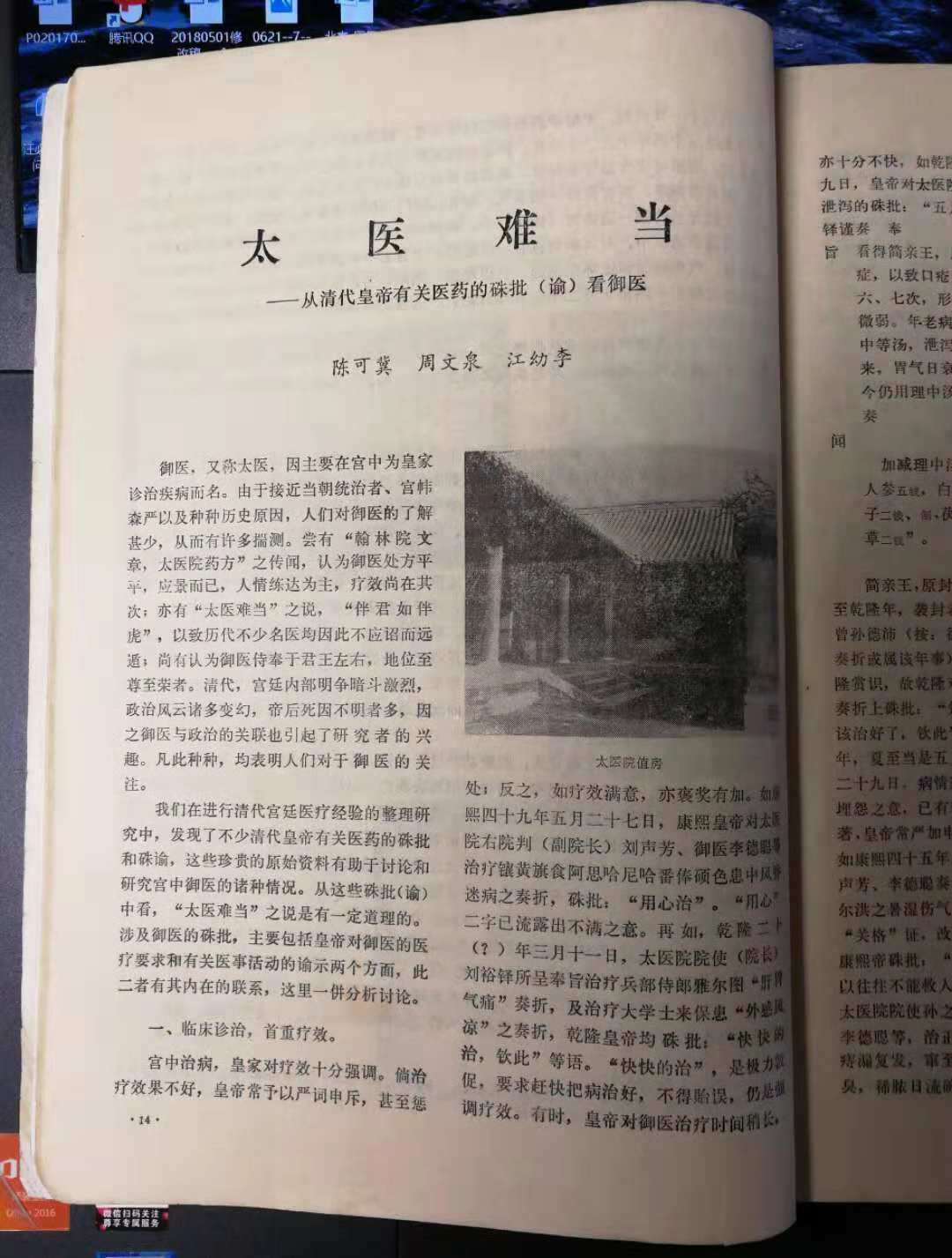
宫中治病,皇家对疗效十分强调。倘治疗效果不好,皇帝常予以严词申斥,甚至惩处;反之,如疗效满意,亦褒奖有加。如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康熙皇帝对太医院右院判(副院长)刘声芳、御医李德聪等治疗镶黄旗食阿思哈尼哈番俸硕色患中风昏迷病之奏折,硃批:“用心治”。“用心”二字已流露出不满之意。再如,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一日,太医院院使(院长)刘裕铎所呈奉旨治疗兵部侍郎雅尔图“肝胃气痛”奏折,及治疗大学士来保患“外感风凉”之奏折,乾隆皇帝均硃批:“快快的治,钦此”等语。“快快的治”,是极力敦促,要求赶快把病治好,不得贻误,仍是强调疗效。有时,皇帝对御医治疗时间稍长,亦十分不快,如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皇帝对太医院院使刘裕铎治疗简亲王泄泻的硃批:“五月二十九日,院使臣刘裕铎谨奏 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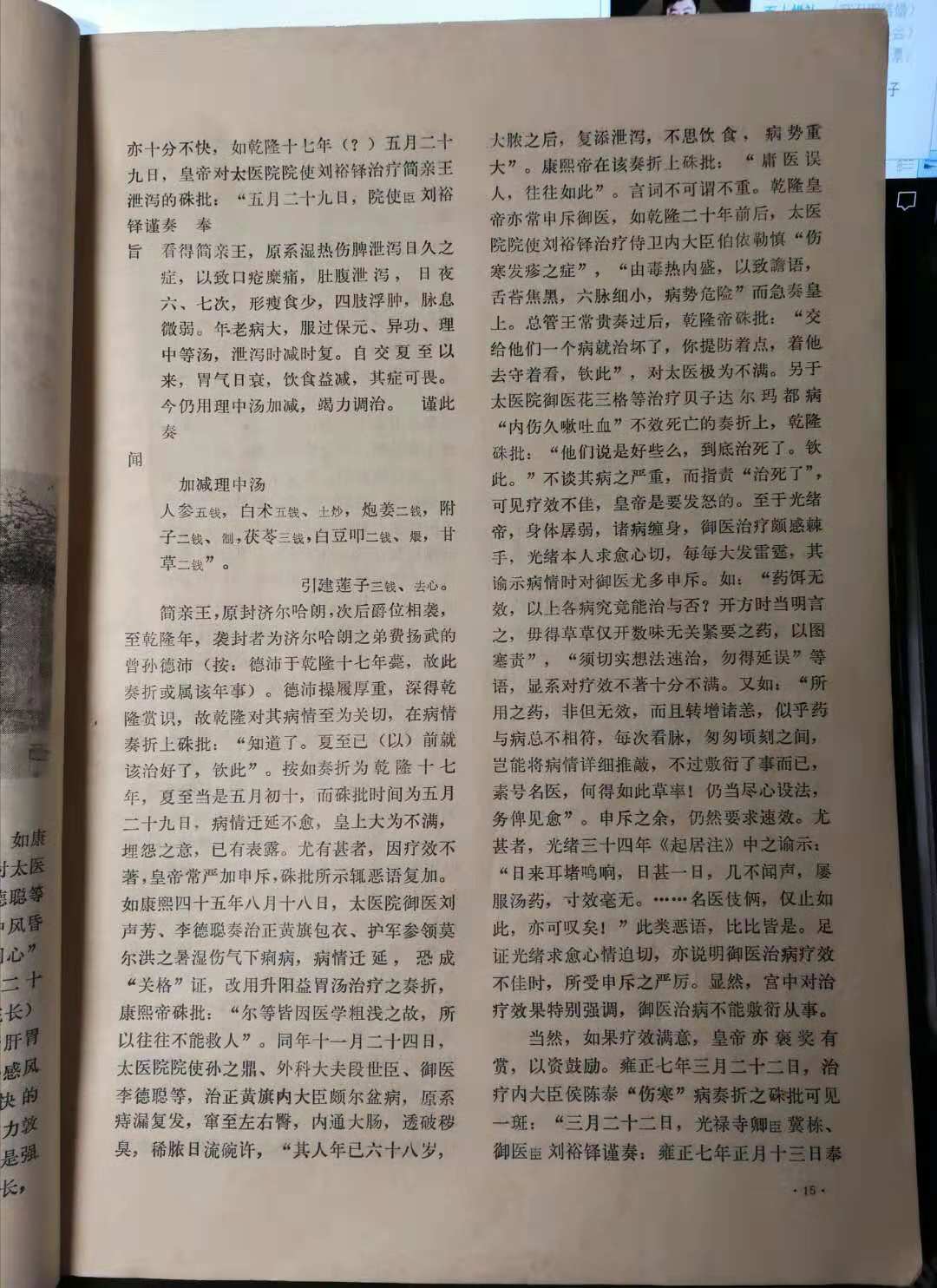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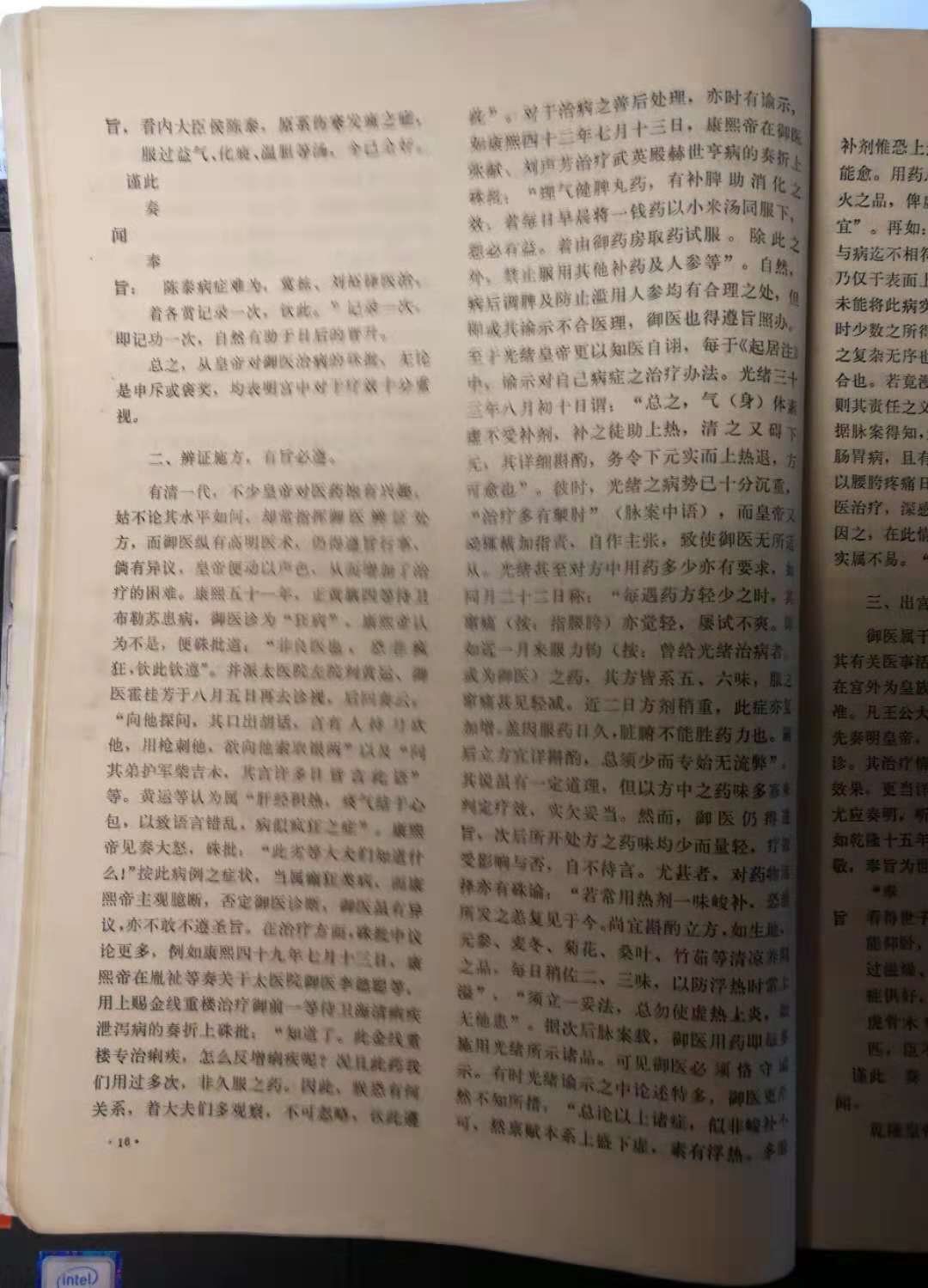
加减理中汤
人参五钱,白术五钱、土炒,炮姜二钱,附子二钱、制,茯苓三钱,白豆叩二钱、煨,甘草二钱”。
引建莲子三钱、去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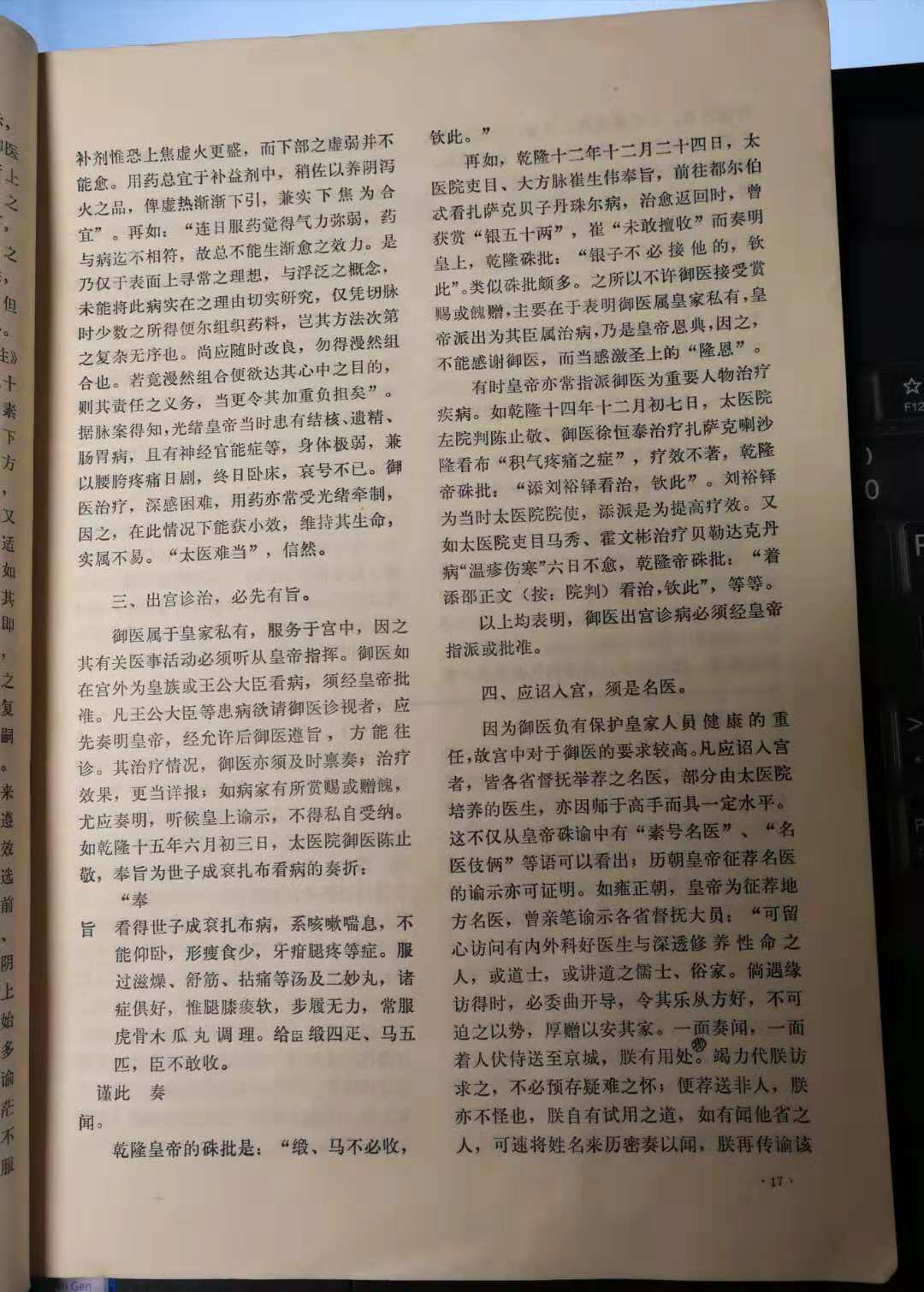
如:“药饵无效,以上各病究竟能治与否?开方时当明言之,毋得草草仅开数味无关紧要之药,以图塞责”,“须切实想法速治,勿得延误”等语,显系对疗效不著十分不满。又如:“所用之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匆匆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仍当尽心设法,务俾见愈”。申斥之余,仍然要求速效。尤甚者,光绪三十四年《起居注》中之谕示:“日来耳堵鸣响,日甚一日,几不闻声,屡服汤药,寸效毫无……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此类恶语,比比皆是。足证光绪求愈心情迫切,亦说明御医治病疗效不佳时,所受申斥之严厉。显然,宫中对治疗效果特别强调,御医治病不能敷衍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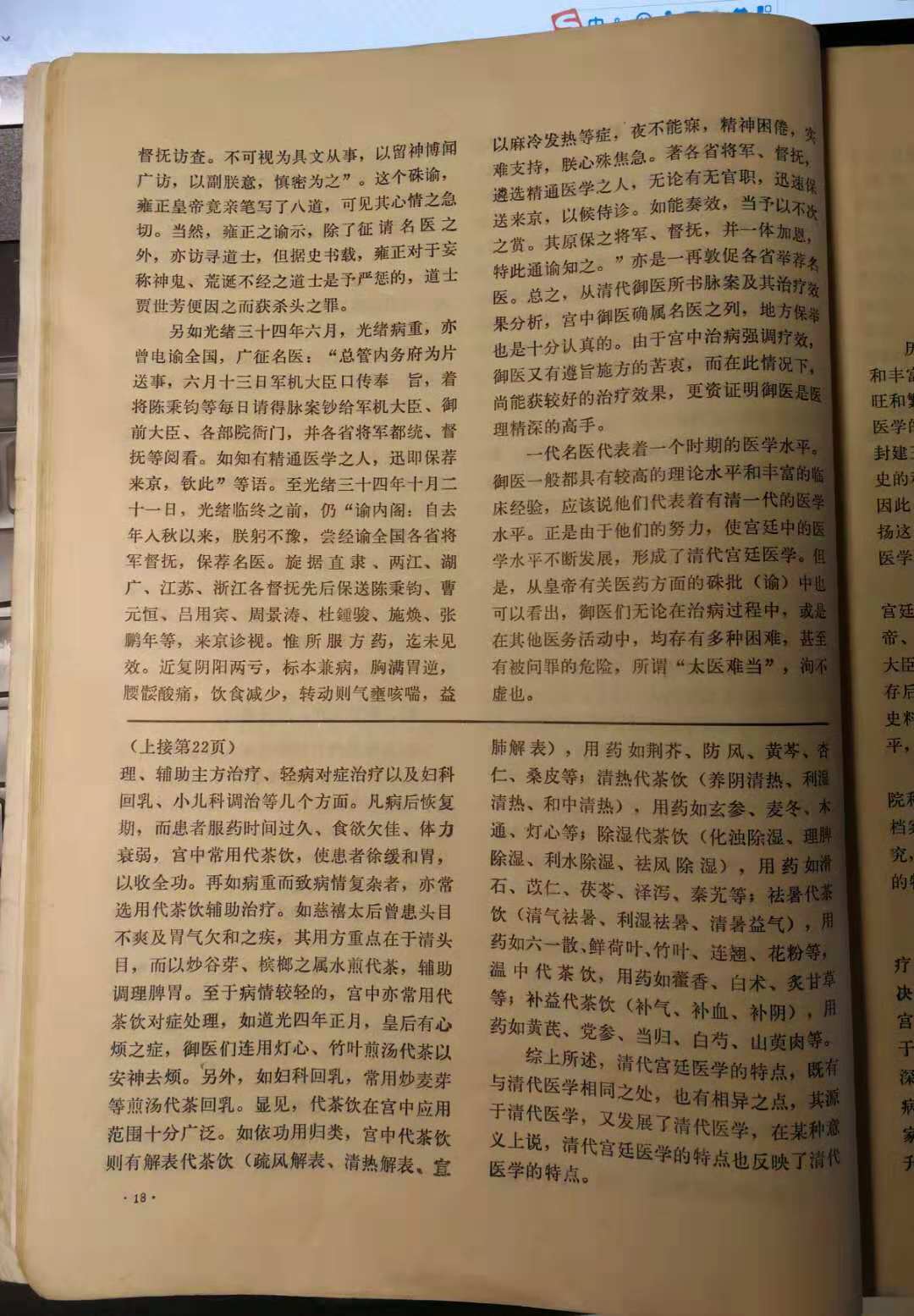
奏
闻
奉
旨:陈泰病症难为,冀栋、刘裕铎医治,着各赏记录一次,钦此。”记录一次,即记功一次,自然有助于日后的晋升。
总之,从皇帝对御医治病的硃批,无论是申斥或褒奖,均表明宫中对于疗效十分重视。
二、辨证施方,有旨必遵。
有清一代,不少皇帝对医药抱有兴趣,姑不论其水平如何,却常指挥御医辨证处方,而御医纵有高明医术,仍得遵旨行事,倘有异议,皇帝便动以声色,从而增加了治疗的困难。康熙五十一年,正黄旗四等侍卫布勒苏患病,御医诊为“狂病”,康熙帝认为不是,便硃批道:“非良医也,恐非疯狂,钦此钦遵”。并派太医院左院判黄运、御医霍桂芳于八月五日再去诊视,后回奏云:“向他探问,其口出胡话,言有人持刀砍他,用枪刺他,欲向他索取银两”以及“问其弟护军柴吉木,其言许多日皆言此语”等。黄运等认为属“肝经积热,痰气结于心包,以致语言错乱,病似疯狂之症”。康熙帝见奏大怒,硃批:“此劣等大夫们知道什么!”按此病例之症状,当属癫狂类病,而康熙帝主观臆断,否定御医诊断,御医虽有异议,亦不敢不遵圣旨。在治疗方面,硃批中议论更多,例如康熙四十九年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胤祉等奏关于太医院御医李德聪等,用上赐金线重楼治疗御前一等侍卫海清痢疾泄泻病的奏折上硃批:“知道了。此金线重楼专治痢疾,怎么反增痢疾呢?况且此药我们用过多次,非久服之药。因此,朕恐有何关系,着大夫们多观察,不可忽略,钦此遵此”。对于治病之善后处理,亦时有谕示,如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御医张献、刘声芳治疗武英殿赫世亨病的奏折上硃批:“理气健脾丸药,有补脾助消化之效,着每日早晨将一钱药以小米汤同服下,想必有益。着由御药房取药试服。除此之外,禁止服用其他补药及人参等”。自然,病后调脾及防止滥用人参均有合理之处,但即或其谕示不合医理,御医也得遵旨照办。至于光绪皇帝更以知医自诩,每于《起居注》中,谕示对自己病症之治疗办法。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十日谓:“总之,气(身)体素虚不受补剂,补之徒助上热,清之又碍下元,其详细斟酌,务令下元实而上热退,方可愈也”。彼时,光绪之病势已十分沉重,“治疗多有掣肘”(脉案中语),而皇帝又动辄横加指责,自作主张,致使御医无所适从。光绪甚至对方中用药多少亦有要求,如同月二十二日称:“每遇药方轻少之时,其窜痛(按:指腰胯)亦觉轻,屡试不爽。即如近一月来服力钧(按:曾给光绪治病者,或为御医)之药,其方皆系五、六味,服之窜痛甚见轻减。近二日方剂稍重,此症亦复加增。盖因服药日久,脏腑不能胜药力也。嗣后立方宜详斟酌,总须少而专始无流弊”。其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以方中之药味多寡来判定疗效,实欠妥当。然而,御医仍得遵旨,次后所开处方之药味均少而量轻,疗效受影响与否,自不待言。尤甚者,对药物选择亦有硃谕:“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须立一妥法,总勿使虚热上炎,始无他患”。据次后脉案载,御医用药即每多施用光绪所示诸品。可见御医必须恪守谕示。有时光绪谕示之中论述特多,御医更茫然不知所措:“总论以上诸症,似非峻补不可,然禀赋本系上盛下虚,素有浮热。多服补剂惟恐上焦虚火更盛,而下部之虚弱并不能愈。用药总宜于补益剂中,稍佐以养阴泻火之品,俾虚热渐渐下引,兼实下焦为合宜”。再如:“连日服药觉得气力弥弱,药与病迄不相符,故总不能生渐愈之效力。是乃仅于表面上寻常之理想,与浮泛之概念,未能将此病实在之理由切实研究,仅凭切脉时少数之所得便尔组织药料,岂其方法次第之复杂无序也。尚应随时改良,勿得漫然组合也。若竟漫然组合便欲达其心中之目的,则其责任之义务,当更令其加重负担矣”。据脉案得知,光绪皇帝当时患有结核、遗精、肠胃病,且有神经官能症等,身体极弱,兼以腰胯疼痛日剧,终日卧床,哀号不已。御医治疗,深感困难,用药亦常受光绪牵制,因之,在此情况下能获小效,维持其生命,实属不易。“太医难当”,信然。
三、出宫诊治,必先有旨。
御医属于皇家私有,服务于宫中,因之其有关医事活动必须听从皇帝指挥。御医如在宫外为皇族或王公大臣看病,须经皇帝批淮。凡王公大臣等患病欲请御医诊视者,应先奏明皇帝,经允许后御医遵旨,方能往诊。其治疗情况,御医亦须及时禀奏;治疗效果,更当详报;如病家有所赏赐或赠餽,尤应奏明,听候皇上谕示,不得私自受纳。如乾隆十五年六月初三日,太医院御医陈止敬,奉旨为世子成袞扎布看病的奏折:“奉
旨 看得世子成袞扎布病,系咳嗽喘息,不能仰卧,形瘦食少,牙疳腿疼等症。服过滋燥、舒筋、拈痛等汤及二妙丸,诸症俱好,惟腿膝痠软,步履无力,常服虎骨木瓜丸调理。给臣缎四疋、马五匹,臣不敢收。谨此 奏
闻。
乾隆皇帝的硃批是:“缎、马不必收,钦此。”
再如,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太医院吏目、大方脉崔生伟奉旨,前往都尔伯忒看扎萨克贝子丹珠尔病,抬愈返回时,曾获赏“银五十两”,崔“未敢擅收”而奏明皇上,乾隆硃批:“银子不必接他的,钦此”。类似硃批颇多。之所以不许御医接受赏赐或金餽赠,主要在于表明御医属皇家私有,皇帝派出为其臣属治病,乃是皇帝恩典,因之,不能感谢御医,而当感激圣上的“隆恩”。
有时皇帝亦常指派御医为重要人物治疗疾病。如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太医院左院判陈止敬、御医徐恒泰治疗扎萨克喇沙隆看布“积气疼痛之症”,疗效不著,乾隆帝硃批:“添刘裕铎看治,钦此”。刘裕铎为当时太医院院使,添派是为提高疗效。又如太医院吏目马秀、霍文彬治疗贝勒达克丹病“温疹伤寒”六日不愈,乾隆帝硃批:“着添邵正文(按:院判)看治,钦此”,等等。
以上均表明,御医出宫诊病必须经皇帝指派或批准。
四、应诏入宫,须是名医。
因为御医负有保护皇家人员健康的重任,故宫中对于御医的要求较高。凡应诏入宫者,皆各省督抚举荐之名医,部分由太医院培养的医生,亦因师于高手而具一定水平。这不仅从皇帝硃谕中有“素号名医”、“名医伎俩”等语可以看出;历朝皇帝征荐名医的谕示亦可证明。如雍正朝,皇帝为征荐地方名医,曾亲笔谕示各省督抚大员:“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透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伏侍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以留神博闻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这个硃谕,雍正皇帝竟亲笔写了八道,可见其心情之急切。当然,雍正之谕示,除了征请名医之外,亦访寻道士,但据史书载,雍正对于妄称神鬼、荒诞不经之道士是予严惩的,道士贾世芳便因之而获杀头之罪。
另如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光绪病重,亦曾电谕全国,广征名医:“总管内务府为片送事,六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口传奉旨,着将陈秉钧等每日请得脉案钞给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各部院衙门,并各省将军都统、督抚等阅看。如知有精通医学之人,迅即保荐来京,钦此”等语。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临终之前,仍“谕内阁:自去年入秋以来,朕躬不豫,尝经谕全国各省将军督抚,保荐名医。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鍾骏、施焕、张鹏年等,来京诊视。惟所服方药,迄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骽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壅咳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倦,实难支持,朕心殊焦急。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以候侍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特此通谕知之。”亦是一再敦促各省举荐名医。总之,从清代御医所书脉案及其治疗效果分析,宫中御医确属名医之列,地方保举也是十分认真的。由于宫中治病强调疗效,御医又有遵旨施方的苦衷,而在此情况下,尚能获较好的治疗效果,更资证明御医是医理精深的高手。
一代名医代表着一个时期的医学水平。御医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应该说他们代表着有清一代的医学水平。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宫廷中的医学水平不断发展,形成了清代宫廷医学。但是,从皇帝有关医药方面的硃批(谕)中也可以看出,御医们无论在治病过程中,或是在其他医务活动中,均存有多种困难,甚至有被问罪的危险,所谓“太医难当”,洵不虚也。(此文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总第17期,14至18页)
